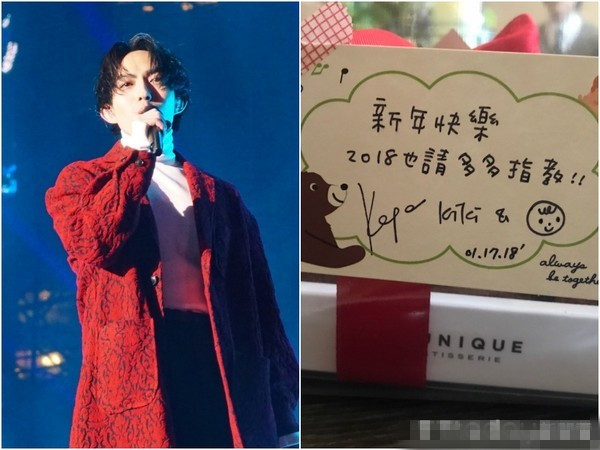电影演员田华简介资料介绍 田华生平经历
2016-12-31 23:28:27 影视资讯
田华的电影艺术生涯,是紧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开始的。
那是一九五○年,当时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准备把著名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在挑选扮演喜儿的演员时,现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原抗敌剧社副社长汪洋推荐了田华。出生在中国北方农村年仅二十二岁的田华,带着一脸的朴实、一身的乡土气息,来到导演和摄影师的面前。大约主要是因为这一点,导演王滨、水华,摄影吴蔚云、钱江共同拍板认定了: 她就是喜儿。
田华当时是华北军区抗敌剧社的演员,年龄虽不大,却已经有近十年的舞台生活,演出过不少的舞蹈、儿童剧、秧歌剧,还参加演出过大型话剧和河北梆子戏。但对电影,她还是陌生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在随剧社进驻张家口后,在这塞上名城的一家电影院里,田华平生第一次看到电影,看的是瑛瑛主演的《灵与肉》。从此,她才知道,在诸多的艺术形式中,还有电影这样一个东西,白白的一块幕布上,竟有活的人、活的故事,是那么生动,那么形象,那么真实,那么富有感人的艺术力量。电影,在田华的心目中,是神奇的,也是神秘的。自那以后,她又有机会看过一些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电影,象《胜利之夜》、《沙漠苦战记》、《科隆斯达海军》、《乡村女教师》、《女政府委员》、《虹》、《巾帼英雄》等。不光为影片中的故事所感动,还为演员不同凡响的表演所折服……但怎么也没有想到,现在自己要演电影了,要走到那块白白的布幕上去了,她是多么兴奋、多么激动啊!

自己能行吗?能演好吗?田华好象没有过多地考虑这样一个普通人在初试时容易想到的问题。她没有畏怯,从容地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她成功了,演活了一个博得了亿万人同情和喜爱的农村姑娘喜儿。“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喜儿,成了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受凌辱的穷苦妇女,跟着共产党求生存、求解放、求幸福的艺术典型。田华一举成了名。电影,它拥有那样广大的观众,无论在城市、在农村,也无论在南国、在北方,绝大多数的人都看过《白毛女》,而凡是看过《白毛女》的人,就知道田华。
田华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白毛女》的导演,充分调动电影艺术手段,使整个影片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增强了时代感,人物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真实可信,这应是主导因素。开拍前,导演给她看过不少有关苏联电影的活页资料,让她熟悉电影的特征; 扮演杨白劳的张守维,天天领着她去看别人拍戏,使她增加了不少感性知识; 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又给了她很多启示,使她对喜儿这一角色的理解,逐步加深。再有当然就是生活了,田华说:“如果我不是生长在河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不是生长在中国落后的旧农村,不是长期战斗、生活、成长在华北根据地,要去塑造好喜儿这个人物,那将是困难的。”
这话一点也不假。
一
田华本姓刘,名天花。说起这名字来,还有点讲头儿。小时候,她皮肤白,留分头,象个男孩子,在家里又最小,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她。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常常因出天花落下一脸大麻子。人们迷信,以为如果叫天花就不出天花了,再加上她又排行“天”字辈,于是就取名 “刘天花”。
一九二八年八月三日,田华出生在河北省唐县南放水村。这是一个百十来户人家的村子,西面紧靠着山,东边是视野开阔的大平原,南边呢,放眼望过去,看得见一架孤零零的山,故名孤山,北边,还有一座状似蒲盖(农家自制的一种草锅盖)的山,家乡的人都叫它蒲盖山。村边有一条小河急急流过,听老人讲,早年间这条河常闹水灾。放水,放水,放了水就不闹灾了,这可能就是“放水村”村名的由来。在这块给了她生命、给了她质朴,同时也使她饱尝了人间辛酸的热土上,田华生活了将近十二年。
据村里的老辈人讲,田华爷爷早先做过贩盐的生意,苦心经营赚了点钱,置了点地,小康生活还过得去。不想后来赔了本,为还债,卖了牲口去了地,家境就败落了。田华父亲排行最小,念过几天书,算得上是个识文断字的先生,可地里的活却做不来。分家另过后,田华兄妹年纪小,帮不上忙,日子就更艰难了。
田华的童年,是在贫困、饥饿和眼泪中度过的。为了帮助妈妈,她不得不过早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推碾子、抬水、拾柴禾,挖野菜,什么活儿都干。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日子更难熬,她就去拾杨穗儿、柳穗儿,捋榆钱儿、榆叶儿,回来交给妈妈做饭、做菜吃。
母亲贤慧、厚道、性情温顺,很会勤俭持家。在田华的记忆里,母亲的脸上却很少有笑容。她总是在忙,从早到晚、从里到外。白天忙完了,夜晚在月光下还要纺棉花。很多次,田华看见妈妈边做针线活、边哼小曲儿; 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有成串成行的眼泪。
那时,她还不理解妈妈,甚至不知道体谅妈妈。看到谁家姑娘穿上了花鞋,谁家吃馒馍、饺子,谁家孩子买杏儿吃,也吵着跟妈妈要,逢到这时,妈妈总是叹口气,什么也不说,等她吵急了。就把她搂在怀里,说: “傻丫头,别不懂事,你怎么能跟人家比呀!人家拨下根汗毛比咱的腰还粗,人家是打着灯笼‘托生’的,谁让你‘托生’在穷人家! ”
看着女儿不解地眨巴着眼睛,妈妈就又象是哄她又象是对自己说: “熬着吧! 什么时候熬到老天爷睁开眼,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你也就能上学、穿花衣裳了! ”
妈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但不是老天爷睁眼,而是来了共产党、八路军。一九三七年年底,国民党南撤,八路军北上抗日,一个骑兵团开过来,驻进了南放水村。减租减息、成立新政府、成立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苦命的妈妈,没有能够亲眼看到这乾坤翻转的变化,过分的忧伤、劳累,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间。田华上学了。
上学后,她参加了儿童团,跟别的孩子一道,拿一杆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捉汉奸……她喜欢唱歌、跳舞,在学校里学的第一首抗日歌曲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学的第一个舞蹈是《蝴蝶姑娘》,边唱边跳,歌词是: “蝴蝶姑娘我问你,你家住在哪里?我家就住在此地百花村里。百花开,请到我的家里来。”田华因为跳得好,被挑选到学校的舞蹈队,还到区上、县上参加歌舞比赛。在她稚嫩的童心里,这一切,无疑都是新奇的、神圣的。
家乡有一种地方戏,叫大秧歌,近似于河北梆子,多演旧戏。逢年过节,村村都要凑起戏班子,演几天戏。田华从小就喜欢看这种“大戏”,还特别喜欢看苦戏、看坤角戏,这些土生土长的民间戏曲,给了她最初的艺术熏陶。
八路军来了以后,文艺活动就多了。一九四○年初夏,有一次,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到邻近南放水的固城村来演出,这下可在十里八村轰动了,男女老少相携相唤,潮水似地涌去看,都要看看八路军的“戏班子”什么样,怎么演。田华跟同学一道,排着整齐的队伍,步行八里去看戏。
节目一开始,就是抗敌剧社小鬼合唱队的合唱。几十号人,清一色的小马裤、吊兜、打绑腿,一个个,可真精神! 坐在台下的田华简直看呆了! 她多么羡慕,羡慕这些年龄跟她相仿佛的小八路! 她想,要是自己能跟他们一样,也穿上军装,也上台唱歌,那该多好啊!
真是天随人愿! 第二天上午,她正在站岗,忽然有人来叫她,让她回学校。到那儿一看,老师正跟两个八路军说话。一个年龄大的,还有一个稍年轻的(后来她才知道那年龄大的是指导员,叫丁鸣,那个年轻的就是葛振邦)。指导员先问她喜欢不喜欢看头天晚上的演出,然后就问她愿不愿意参军、愿不愿意参加抗敌剧社。这还用说么?昨天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参军了,穿上了军装,也是小马裤、吊兜、打绑腿……“得回家问问我爸爸……”她羞怯地这样回答,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
爸爸同意了。她自己呢,想到就要跟着生人离开家,小小的一颗心却慌了。长这么大,连十里地以外的地方都没去过,最远去过姥姥家,离她们村正巧十里,而且是住几天就回来。这次一走,知道要去多远!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十四岁的姐姐一边帮她收拾东西,一边抹眼泪。
跟她一同走的,还有村里的另一个女孩子。走时,村长代表全村乡亲,给她俩一人五块钱边区票,让她们小心揣在腰里。村长、老师、爸爸、姐姐,还有一些乡亲依依不舍地送她们到村口。
故乡,渐渐地远了。一别啊,就是几十年! 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田华从没有忘记过故乡,没有忘记故乡的亲人,没有忘记故乡对她的哺育,没有忘记故乡给予她的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