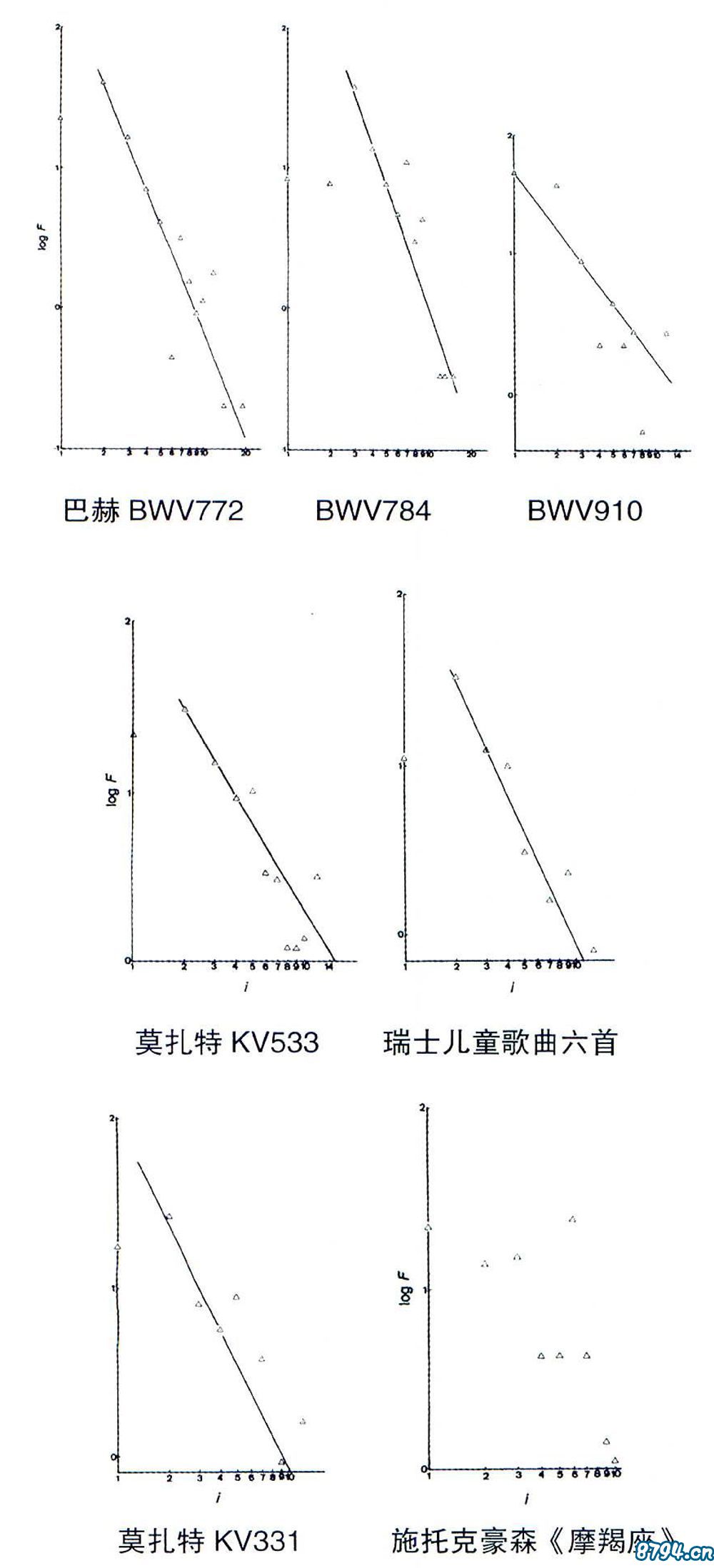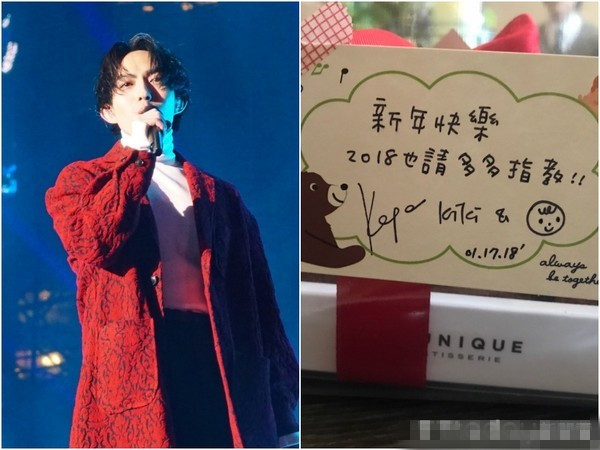对音乐学研究中“跨学科”问题的认识
2014-10-01 16:08:19 音乐资讯
《音乐研究》编辑部此番召开“跨界”问题学术研讨会,对于当前我国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很有意义。会上来自音乐学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就“跨界”问题的发高对我很有启发,我也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认识,以就教于大家。
按我的理解,所谓“跨界”问题的实质,不外乎是扩大音乐学学科的学术视野,松动学科之间的壁垒,在这个基础上深化学科的内涵,推动学科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我先后于2002年和200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扩大音乐学学科的视野,使音乐学学科从其他相关的人文学科那里吸取滋养,以及实现音乐学学科内部各子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当今各人文学科、音乐学的各子学科已呈现迅速发展的情势下,扩大音乐学学科自己的学术视野就更显得重要和迫切。如果我们的眼光只同于学科内部,甚至只囿于子学科内部,忽视甚至放弃在不同学科之间、不同子学科之间的边缘和交叉点上寻找学术的新的生长点,那么,在音乐学领域实现真正的创新和突破,恐怕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一个音乐学家在学术上应该放开自己的眼光,拓宽自己的视野,时刻关注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以及各子学科中新的成果和信息,这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先哲恩格斯早在1876年他的一部著作中就已经有过异常精辟的论述:“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能把它们看作运动的东西,而是看作静止的东西;不是看作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作活的东西,而是看作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的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看见树木,不见森林。”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当代的两位哲学一人文大师张岱年和季羡林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哲人的思维方式时,特别强调先哲与西方擅长的分析思维有所不同的“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观念。
近百年来,恩格斯强调“在广泛的总的联系”中对事物进行考察的思想,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实现,在这个领域中由于相当广泛地实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和融合,科学技术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而这个问题在人文学科领域,包括音乐学学科,也已摆在面前。
在我看来,音乐学学科的“跨学科”问题可以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音乐学学科与其相关的上方学科领域的关系,其中包括诸如哲学、历史学、艺术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音响学,以及甚至与自然科学相关的某些学科等等诸多学科领域;第二个层次是音乐学学科内部的子学科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诸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民族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形态学(即音乐技术理论)、音乐分析学、乐律学、音乐考古学、音乐文字学(记谱法)、音乐表演理论等等诸子学科领域。
在第一个层次中,我倾向于认为,音乐学与其相关的上方诸学科领域的关系并不是“跨学科”关系,更不是所谓“跨界”,音乐学并不是要“跨入”到哲学、历史学、美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中去,而是从这些学科领域中吸取理论资源,获得理论支撑,提升自身的理论内涵,以更透彻、深入地认识学科自身的性质。
在第二个层次中,也即在音乐学学科内部的上述一系列子学科之间,则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问题。也就是说,在诸如音乐史学、音乐美学、音乐民族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心理学、音乐形态学、音乐分析学、音乐表演学等等之间实现相互间的联系、融合、渗透,相互阐释乃至相互支撑、相互印证。此时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或是在学科相互跨越的过程中,强化、丰富了某一子学科自身的内涵;甚或是在跨越过程中模糊了、突破了某些子学科之间的界限,形成某种新的、具有多元化性质的、相互间实现深度融合和渗透的学科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