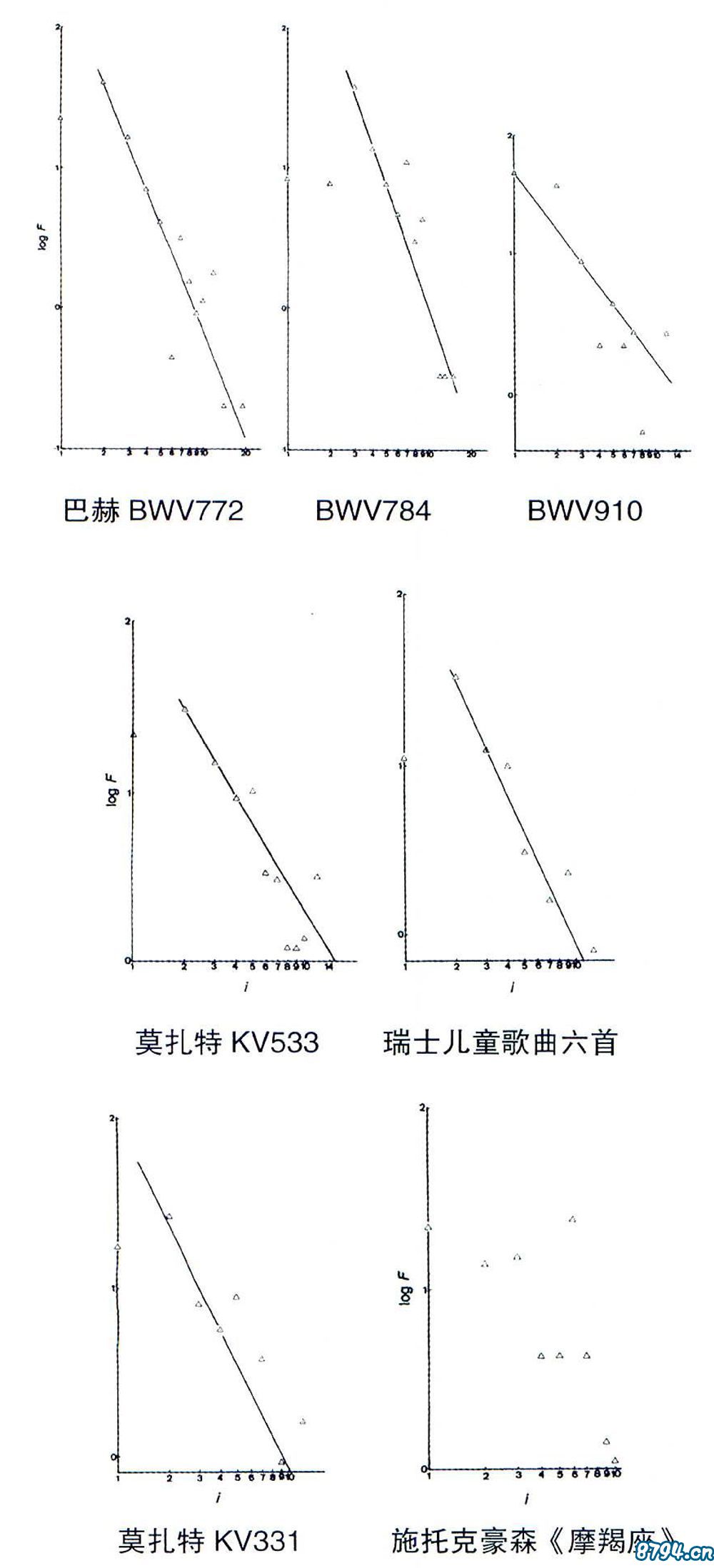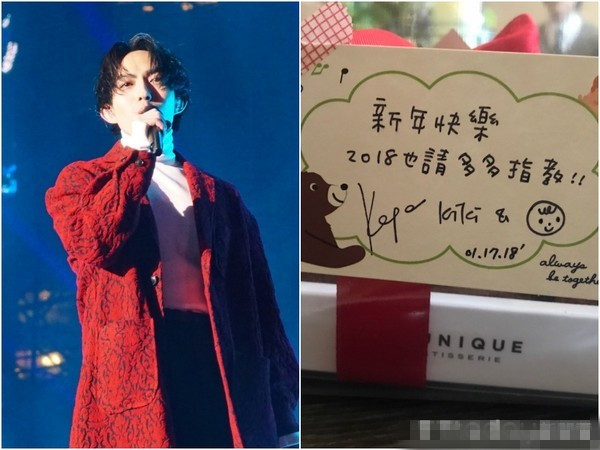音乐学学科结构变动的意义:以汉文化区音乐研究为例
2014-10-01 16:11:10 音乐资讯
一、关于音乐学学科结构的变动
《音乐研究》编辑部郑重举行“跨界”问题研讨会,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中国音乐研究者为什么会在现在讨论“跨界”?编辑部在会议通知中说:这是因为,近年来在音乐学领域兴起了“跨界”、“跨学科”、“接通”等概念,“这些概念意味着传统的学科意识、学科界域与治学方法正在发生变化。”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跨界”会议意味着,我们正在面临音乐学学科结构的变动。
不过,若追溯历史,那么可以知道:古代的中国学者是不作这种讨论的,因为那时并没有明显的学科分界。古代学人崇尚的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君子不器”,“道未始有封”。尽管他们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但他们并不讲究“学”的界分。“君子不器”是孔子的话,意思是君子所学不限于一才一艺,而要无所不施。“道未始有封”是庄子的话,意思是道本来就不需要分界,不需要限定。古人是不是对知识体系作过分类呢?当然作过,这就是从汉代到清代目录学家们所创建的多种图书分类。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目录学分类都没有把“音乐”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而是把现在所谓“音乐”划作大雅之乐、乐府余音、杂艺之声三部分,分别归人经部(雅乐书类)、集部(词曲书类)、子部(杂艺书类)。这意味着,所谓“音乐”,所谓“音乐学”,所谓“跨界”,其实都是产生于现代的学术概念;提倡音乐学的跨界研究,其实是提倡向某种综合传统的复归。
若把观察历史的眼光移近一点,我们又知道:现在的学科分界,其实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新式教育的产物,是因现代课堂的教学需要而产生的。古今的学术研究都不会要求这种分界。凡有研究经验的学者都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每个对象,都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运用多种学科方法去认识,这样的认识才具有深刻性和全面性。与此相反,教学则必须分科。这一点又意味着,现在讲“跨界”,其实是讲研究范式对于教学范式的突破。换言之,音乐学学科结构的变动,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即使从逻辑上看,我们也知道:“跨界”的概念是由分界引起的,“接通”的概念则缘于学科之间的不通。正因为这样,学科分界产生之时,便是“跨界”、“接通”的慨念孕育之日。于是我们看到,当人们发现分界的局限性,而需要扩大学术视野、综合运用多种学科资料和方法的时候,就提出了“跨界”、“接通”等概念。因此,这两个概念构成了一百年来学术发展的重要经验。比如陈寅恪先生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义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同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同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些话,说的就是研究视野、研究资料从中国向外国的跨界,以及考古学与文献学的接通,西方理论与中国材料的接通。由于“跨界”、“接通”的结果是学科结构的变动,所以陈先生义说:这三者“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总之,“跨界”、“接通”是两个有充分合理性的概念,具有普遍意义,并不是音乐学研究者的专利。因为只要有分界,就会有“跨界”;只要有不通,就会有人提出“接通”。一有的朋友担心出现“走出去,回不来”的局面,提出“客位学科不能代替本位学科”,我认为这两种忧虑都是不必要的。不要说研究者个人的学科转型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从音乐学学科的角度看,它的结构变动,也是自然的、必然的。在巾同近现代音乐学者的群体中,这两方面都有很多现成的例子。比如王光祈,毕业于法律专业,后赴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学;赵元任,康乃尔大学物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忻学博士;潘怀素,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沈知白,上海工部局师范学院毕业,音乐素养全凭自学;黄翔鹏,毕业于金陵大学物理学系,后改学音乐;赵宋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改学音乐。这些人的经历证明,当今这个中国音乐学,是因为很多“外行人”的跨界而造成的。而关于音乐学学科的结构变动,则可以看看一百年来音乐学的发展:那些新生的音乐学々业,比如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音乐社会学、音乐美学、音乐治疗学等等,其实都是“跨界”和“接通”的产物在这些专业当中,何为主位,何为客位,是很难画出明确界线的。
二、一个“外行”的跨界经验
上面所说“一百年来学术发展的重要经验”,自然也包括我们这代人的经验,比如我本人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便是从跨界研究开始的。
我原是一名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就为解决中国古代义学的问题而进入了音乐研究领域。其中一个缘故,是我曾经师从王运熙、任中敏(二北、半塘)这两位有跨界倾向的先生,任先生的跨界活动开始于1920年前后,原冈是他的老师——吴梅(瞿安)教授——把二胡、笛子、词曲和昆曲演唱带进了北京大学的课堂。这是一件曾经引起轰动的事情,因为有人认为它代表了音乐对文学的“僭越”和“覆盖”。但这件事却得到一批学术青年的崇奉和追随。这样就产生了作为学术大家的任中敏先生:他以毕乍之力,创建了散文学、唐代文艺学两门学川,进而使中国音乐文学学科初具规模;同时也产生了夏承焘、唐圭璋、龙渝牛、卢前、王季思等一批杰出学者:他们使20世纪的词曲学史充满辉煌。王运熙先生的跨界活动同样始于青年时期。他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便开始了对乐府诗、清商曲和六朝民歌的研究。他重视研究音乐制度的变迁、音乐机构的创设和音乐的地域化特色,由此较深刻地阐明了一系列文学问题。任先生和王先生都是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跨界到中国音乐史研究的。他们的经验表明:音乐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存在相互取资的关系。“跨界”不止是音乐学对于其他学科的要求,而且是其他学科对于音乐学的要求。正是通过跨界,音乐学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以上情况还说明:我们讲“跨界”和“接通”,是因为相关学科之间本来就有内在的相通。音乐和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部主流的中国文学史(由诗而词,由词而曲的发展史),从形式上看,其实就是一部歌唱史,或者说是一部音乐与文学相互作用的历史。一般来说,文学代表了这个历史事物的内容,音乐代表了这个历史事物的形式。不了解形式,就不可能了解内容。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跨过界来,和音乐学接通。但从另一面看,中国音乐又是一个拥有多种向度的事物,它既可以作为有组织的音响而存在,也可以作为制度事象或文化事象而存在。因此,音乐研究至少需要四种人:一是善于辨音和记音的人,二是懂得各种音乐组织的人,三是有能力搜集和研究古往今来的音乐记录的人,四是通晓作为音乐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这样一来,音乐学界又需要文史研究者跨过界来,和音乐学接通。1985年,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对隋唐五代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作了全面考察;1986年初,我来到北京找黄翔鹏先生,要求在音乐学方面深造;1989年,我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的一员,负责历史文献方向的工作。前两件事,其实便反映了文学研究向音乐研究跨界和接通的需要;后一件事,则反映了音乐研究对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前来跨界和接通的需要。也就是说,中国音乐学同其他学科的跨界和接通,其动力,既来源于其他学科所提出的要求,也来源于本学科所提出的要求。
1993年,我开始在扬州大学招收博士研究生。博士生教学是学术性的教学,要求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而非再现性人才。这使我们有条件也迫切需要进行“跨界”和“接通”的教学试验。于是,我所在的博士点进行了以下项目:
(一)中国戏剧史研究和民族学的结合。一位长年生活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博士生,把他对云南各民族表演艺术的考察成果同中国早期表演艺术资料相结合,建立起关于中国早期戏剧形态体系的认识,重新解释了中国戏剧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