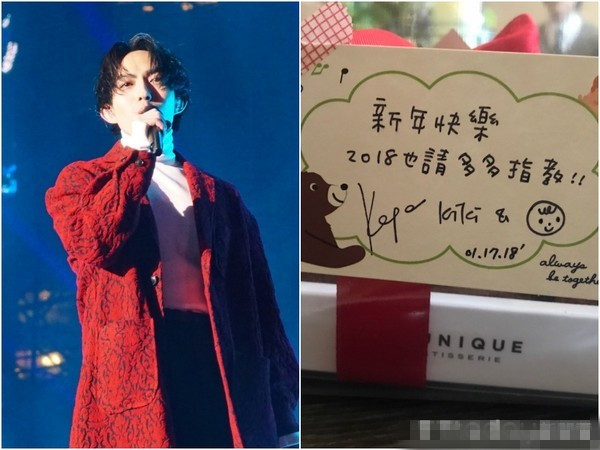音乐学研究中的“跨界”认识[第2页]
2014-10-01 16:14:50 音乐资讯
再以音乐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为例,这也是最能体现音乐学研究对跨界方法运用的一个领域。社会学是以研究人和人的总体特征为核心的综合性、实用性社会科学。社会学从各个角度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社会问题,而生活作为音乐文化表现的核心所在,音乐文化全面地参与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和角落,这样一来,音乐艺术和社会学的核心对象是几近一致的。并且,音乐艺术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物质、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是建立现代生活方式的重要促进因素。
譬如,论及1803年前后的贝多芬,音乐史上都会认为这一年是他“新风格的开端”,原因在于他于这一年完成了《第三交响曲》(“英雄”)的创作。也许作为代表贝多芬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转折点,《第三交响曲》着实是他音乐风格的分水岭。从音乐文本的研究中,有关《第三交响曲》这部作品的时机,它的新风格,以及他的创造性进入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长期以来已被有关贝多芬的生活和音乐的无数研究所论及。然而,这些论述是否就为我们提供了那一时期渐趋完整的贝多芬呢?答案肯定是值得拷问的。但如果在这一时期置人社会学、经济学方法论加以剖析,无疑可以给我们一定偏于定性的说法。
历史回放到1800-1802年前后。1792年,当22岁的贝多芬以学生身份到达维也纳时,立即吸引了维也纳贵族的注意。1800年4月2日,在一场音乐会上,跟在莫扎特、海顿的作品之后,贝多芬为维也纳贵族首演了他创作的五首作品,开始出人头地。1801年夏,在给儿时玩伴魏格勒的信中,贝多芬描述了他的状况:利希诺夫斯基亲王给他600弗罗林的年薪,他的作品有六七个出版商等着出版,而且依他开出的价格。并说,随着他的知名度的提高,他每年都可以举办音乐会。在此期间,贝多芬靠各种音乐活动的收入,便可以过着谈不上奢侈但也十分舒适的生活。然而,从1802年起,贝多芬需要寻找更多的收入来源以弥补食品、租金、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物价上涨。他的经济困难的发生适逢奥地利经济状况的恶化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时的通胀率已达40%。
在1802年冬天,贝多芬尝试租剧院来举办公开音乐会,同时开始与著名的莱比锡出版商布劳考普夫(Breitkopf)和黑特尔(H/irtel)联系。对于举行公开音乐会,之前他只在1800年4月在维也纳举办过一次。然而,在维也纳一年中只有几个晚上没有歌剧演出时才能租到剧院,即使租到,也要受宫廷剧院管理人员的严格控制。事实上,贝多芬从来没有容易地租到宫廷剧院。他在维也纳居住的35年中,总共只举办过8场公开音乐会。对于与出版社的交往,他第一次卖给出版社的是《c大调弦乐五重奏》(Op.29,1801),获利50杜卡特,为出版商第一次支付贝多芬较高的费用。与此同时,贝多芬的耳疾使其产生抑郁沮丧心情,以至于在1802年10月写下海利根施塔特遗嘱,描述了这一年堪称个人分水岭的状况。贝多芬承认他的听力困难不可逆转,无法治愈,涉及经济因素。作为教师,他的教学生涯不可避免地结束,意味着迟早要有新的收入来源;作为钢琴家,就在1802年底,他对在贵族沙龙的社交演出活动已经感到不舒服,萌生了减少去演出的念头,其后的演出频率渐少,究竟是何原因不得而知,以致到1808年他设法进行了最后一次演出后而淡出了舞台。源于贵族的赞助也因经济危机受阻,1802年底,贝多芬考虑离开维也纳去巴黎。
1803年初,贝多芬得到维也纳剧院总监委约歌剧创作的机会。尽管创作计划告吹,但贝多芬因这份合同获得剧院提供的免费公寓,并在4月5日利用剧院举办了音乐会。由于票价非常高,贝多芬挣得1800弗罗林,这一标准堪与同时期维也纳报道的音乐会最高收益相比。原本是要创作委约歌剧的,但贝多芬在举行新作品音乐会后的5月份,决定把剩余的时间用来创作一部新的交响曲,一部宏大的戏剧性交响曲,甚至想到是下一场公开音乐会的主打曲。贝多芬“新风格”的分水岭在1803年5月明晰地显露出来,无疑与前一年10月立下的遗嘱的主要思想有关,即要以审美的、为特定的听众在特定情况下演出而创作——贝多芬认为是“艺术留住了他”。主观上的分析只能如此。客观上呢,维也纳当时的经济情况——人们真正的经济需要和赚钱机会,这一点贝多芬在1803年4月5日音乐会上的《第二交响曲》为所获得的赞美评论流露出高兴之情,显然会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历史概念的“决定系数”——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多重原因,但每个原因本身似乎就足够了。循此理论,我们不难看到《第三交响曲》之所以代表了贝多芬的风格分水岭,从他的听力的困难,导致作曲伴随着更为主观的严肃性,一方面使自己的创作愈来愈成熟,一方面创作出来的作品与音乐爱好者的接受能力相背离;从他对法国的情结和对英雄主义的推崇;从他所处时代维也纳经济因素的遽变,在心理上同时也在音乐上形成了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新风格”。1803年以后的五年中,贝多芬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出版费。
在此,我们采用学科跨界分析了贝多芬1803年前后风格转型的因由。我们甚至还可以在此结论上进行一番历史观照。众所周知,音乐艺术所表达的语境意义是多重的。我们在欣赏《第三交响曲》时,如同达尔豪斯所说,欣赏之前要养成必要的历史知识与历史判断。因为这些历史的理解已经融入在传统之中。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审美经验就会更加丰富。只有具有相应的审美储备与智性经验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该作品所有的智性经验和历史特征,我们的审美经验才会达到相当的高度。因为有了前面的社会学的综合性,到这一步,融入哲学层次、历史学层次的研究,实现不同层次间的贯通,我们的研究既能抽象,又能具体;既有经验实证,又有逻辑推理,上下通达,跨界研究带来的纵深感、穿透力是不言而喻的。
“海阔天空我自飞”。不可否认,跨界研究是我们的音乐学研究实现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解决学科前沿问题能力的必要措施,也是当今学界音乐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尤其在当今所面临的比以往要复杂得多的环境中,在历史变化过程中形成的音乐文化,其发展和变化既有自身系统的变化,也有外力的作用。倘若要认识外在形态抑或其变化的因由,跨界研究无疑可以给出自己独特的解释。所以我们主张,尽管在研究中可能存在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但允许多元并存,实现学科的跨界,打破森严的学科壁垒,回归到原本就是“无界”的学科自然状态。研究中抱持跨界观念,坚守研究者的自由意志和对学术的热情。因为,学科的发展注定了要进一步超越学科。
作者附言:本文为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古良贱乐人社会身份的形成与中古伎乐的转型”(项目编号11 BD041)阶段性成果;2012年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陕西音乐社会史·汉代部分”(项目编号1202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安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