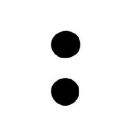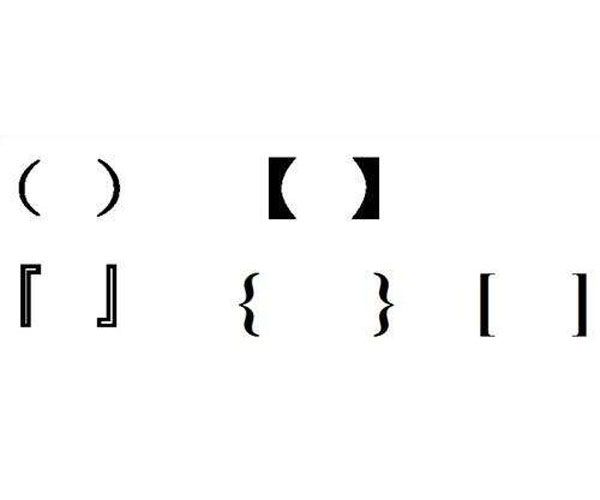东北满族:柳条边外[第2页]
2017-07-05 16:00:56 知识
东北人口结构发生本质性变化的年代,是在清末民初。缺少土地的关内山东、河北农民背井离乡“闯关东”的大潮,就在这个时期达到巅峰。这次规模浩大的移民潮,不仅导致东北人口激增,更不可逆转地导致了东北地区 “满洲社会”的彻底衰落,从此,除了一些极为偏僻的山村,东北几乎再无满族单一民族的聚居社区。
清朝的统治者基于自身民族政权的考虑,一直试图在东北保持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国语骑射”的文化特征。但生产方式是一种支配历史发展的更大的力量,远不是统治者可以规定的。汉族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一边使“柳条边”形同虚设,另一边也让东北土著人口渐渐接受了比渔猎文化 “更先进”的农耕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努尔哈赤创造出满族,是英雄创造历史的“铁证”,那么汉族移民进入东北并成为地域性主导性人口集团的过程,则显然是“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典型证据。
东北这片土地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合农耕。从辽河流域到三江流域,纵贯东北的辽阔平原和低山丘陵地带,土壤肥沃,降水丰沛,无疑是农耕的天堂。然而,17世纪以前女真人(满族) 的传统生产方式是以渔猎为主,这和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遍布东北的茂密森林和水量丰沛的江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环境基础。
明清两季东北地区的汉人渐渐增多,先是辽东,而后向北深入东北的腹地。汉族农民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也成为满族人口农业上的老师,引导着满族人渐渐走上农耕的道路。这是一次生产方式的转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北居民的文化特征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那里的社会文化意识渐渐被农业文明主宰。近代以后,随着大量关内汉族农民的到来,东北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被彻底改变,东北终于成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区域性主体人群从渔猎向农耕生产方式的转变造成环境的变化,大片的森林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是农田;以打鱼狩猎为谋生手段的人口边界沿着森林线的变化向北部和东部退缩移动,终于在东北东部山区与西部草原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断扩大的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区。曾经的渔猎生活只在极为偏远的地区成为历史的遗痕,如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他们直到新中国成立仍然保持着这种生产方式,但就东北满族的多数人口来说,他们已渐渐成为和汉人一样的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
汉族农民人口集团之所以能在东北站稳脚跟并渐渐成为主导,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这个集团渐渐增大的人口规模,最终使之成为东北地区占有压倒性优势的主体人群。同时由于关内汉族移民绝大多数是赤贫的农民,他们的基本生存技能就是会种地——这种技能无疑普遍高于满人旗人,加上他们不仅有不惟守成的冒险精神,更有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文化传统,这样一方面许多新的耕地被开辟出来,另一方面也渐渐使原本属于满人旗人的土地流转到汉人农民手中。第二个原因是东北土著居民——满族对汉族人口与文化的自然接纳。尽管有清一代八旗人口受到政治性的优待和保护,但当农耕文明成为东北地区的主导文化时,精于骑射的满洲文化便从原来明清战争时的“优势文化”演变成日常耕作中的“劣势文化”,这深刻地改变了满族的实际文化处境,特别是在底层社会。同时不可忽视的是,满洲不仅原来人口就少,身边还伴有大量的“汉军旗人”,因此尽管无法准确判断年代与时间,但满汉间文化差别的渐渐模糊应该是很早就发生了,甚至可以猜测这个时间点并不晚于满族的最终形成之时。
“九一八”事变(1931年) 后响彻全中国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深情地唱道:“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实际上,东北的主要农作物直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是大豆、高粱,如今极为常见的玉米种植,当时还没有大面积普及。而东北水稻种植的缘起则与朝鲜族有关,特别是日本殖民东北的时期,迁徙了大量朝鲜人到东北,教当地人如何种水稻。
在经济生存方式上早已渐渐趋同的东北满族和汉族,在清朝统治的近 300年光阴中仍然保持了相当清晰的族群社会边界——满汉畛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是清朝民族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清廷必须维持满汉畛域以巩固自身的权力基础。在整个有清一代,满汉畛域在国家层面是政权强力推行的制度,需要草根社会的服从,但草根社会首要的考虑是现实的生存逻辑。当政权能够依据民族身份提供优化资源时,底层的民族认同就得到了强化。然而,族群认同有其自身的内在特质,政权“自上而下”地放大或缩小这种特质,或片面解释或强化这种性质,都需要靠政权的资源投入。一旦政权无法或不愿意继续投入这种资源,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由外部力量建构起来的族群认同就可能自然消解或变形。
因此,依靠政治力量维续的族群认同,必然深受政治力量兴衰的影响。一旦政治力量的权威弱化,立即出现衰减。经过清朝覆灭到今天,百年之后,满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至少在东北地区的经济生活层面,已经完全融合了。